导演耿军:我的电影不是东北量贩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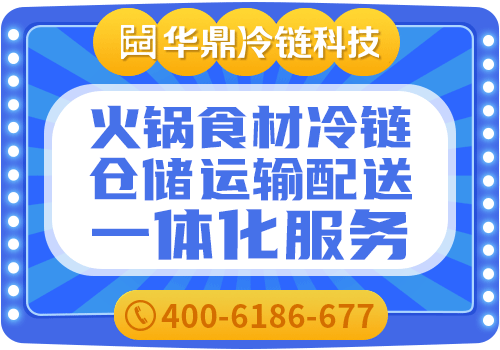
今年是耿军拍电影的第二十年,长短剧情片、纪录片作品加在一起有十几部,在行业内,拥有这个作品量的导演不算多,耿军是其中最不出名的一个,起码在观众认知层面如此。
在电影《东北虎》之前,耿军的所有作品都没有在国内公开上映过,盗版和机构放映成了最重要的观看渠道,因此一度被归为地下电影导演。事实上,耿军的作品与地下电影有很大区别,他的题材并不敏感,风格也不实验,虽然常带有强烈的批判现实意识,但故事拍得都很规矩。
耿军是黑龙江鹤岗人,电影里的故事也多在鹤岗发生,主要演员刚哥、勇哥、薛宝鹤是耿军生活中的朋友,他们在电影中彼此依赖,也彼此成就。
2021年6月19日,上海电影节金爵奖将最佳影片颁给了电影《东北虎》,外界把这次获奖看作耿军职业上的分水岭,但让耿军影迷兴奋的是,“鹤岗宇宙”在这部电影里完成了首次集结。
获奖后,“鹤岗宇宙”连着庆祝了几天,耿军表态允许膨胀,有度就可以。回到北京后,创作之外的杂事开始多了起来,他仍租住在通州的房子里,过着简单的日子,电影似乎从来没有改善过他的生活,但他的人生却结结实实地被电影改变了。随着《东北虎》的上映,耿军之前的作品也开始受到关注,我们和他聊了聊他在电影里度过的二十年。
职业、非职业演员,有差别,但不大
新京报:《东北虎》在你手上已经放了好多年,现在这个版本和最初你心里那个《东北虎》相似度有多少?
耿军:我是2012年写完的剧本,早于《锤子镰刀都休息》和《轻松+愉快》,所以《东北虎》最初的形态更接近于我之前的那部电影《青年》。2018年春天的时候,我根据最初的那个剧本,做了差不多40%的修改。在变换的过程中,它其实变得更柔和了一些。我中间有一两年走了弯路,想把这个东西弄成类型片什么的,给自己弄得有点儿迷糊。
新京报:跟资本市场有关系?
耿军:我跟资本没关系,《锤子镰刀都休息》在金马得完短片奖后(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有些公司找过来问下面做什么,聊到了这个,最后没做。所以我才在2015年拍了《轻松+愉快》,因为《东北虎》找不到钱,做不成,《轻松+愉快》相对预算比较少,容易操作。
新京报:《东北虎》预算更高,是因为要使用职业演员的原因吗?
耿军:其实一开始要改成类型片的那两个公司,都已经开始码演员了,但码的那些演员对这个故事来说,并不是特别合适,只是符合他们的商业要求。起初这事还比较友好,市面上的演员你觉得谁合适演那个男的,谁合适演这个女主角,之后就是聊市场,有点儿像温水煮青蛙,弄来弄去就是谁的流量大,谁的票房最好。
新京报:职业演员和非职业演员,在你作品里的表演方式差别大吗?
耿军:职业演员和非职业演员肯定会有区别。一个电影,首先要把本身的节奏感,气质调到一个频道上,这需要靠表演完成,因此表演也要调到一个频道,但这一点儿不难,因为好的演员一定有很多种方法,所以合作职业或非职业演员,差别有,但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新京报:之前你选的演员都不太常规,比如《轻松+愉快》里那个悍匪老太太,实在太好笑了。
耿军:那个是挺逗的,《轻松+愉快》那一年放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业内人问我这个老太太在哪找的?那个老太太其实是我们当地特别普通的一个人,我找演员的时候,在当地发了个消息,有很多人过来面试。她不会演戏,但我喜欢她的面孔,到后来还是决定找她来演。因为第一次演戏,完成起来没那么容易,但是我们慢慢拍,什么时候拍好什么时候算。其实她的那一场戏,我们拍了整整两天的时间。最后呈现出来确实非常好。
新京报:她的荒诞程度让整部荒诞电影都显得正常了,当时是有意识地追求这些意外感吗?
耿军:其实我自己要追求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不太容易评论。有时一个电影弄完,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再跟大家一起看时,会特别恍惚,我想,这是我干的吗?
新京报: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耿军:我自己没想做电影评论的事,所以当有的观众,有的影迷聊出他们的看法时,那个电影对我来说也挺陌生的。我有时不太容易说清自己是怎么回事,或者自己作品是怎么回事,概括总结自己,我觉得是给自己画了一个圈,画完后你又想翻出去想跳出去,还不如不画这个圈。我其实完完全全是感性支配创作,这也是我的剧本修改时间会特别长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哪里情节写出来了也对,但也不够有意思,我会想怎么才能有点儿意思?我会在这件事上磨很长时间。
新京报:私人的趣味反倒更容易抓住观众。
耿军:对,比如你刚才说的那个老太太那场戏,但你再问那场戏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自己都恍惚,虽然没有多长时间,但是我知道这么写是够意思的。只有这样才会对另外两个骗子,造成心灵上的那种粉碎性骨折。这个人的出现,就是为了干灭他们,那这个灭霸是谁呢,是一个孔武有力的人还是一个凶神恶煞的人?不,她是一个从小卖店里出来的老人。其实我所有的这些创作想法,都来自于我的趣味和那种审美的趋向性。
新京报:我一直以为这是个精心设计过的人物。
耿军:有一些记者或电影从业者,也跟你一样聊到了这场戏,会聊这个人的形象。我觉得你们这么认为还真挺好的,这是没问题的,因为电影其实属于观众。
新京报:用两天时间拍她一场戏,就一点儿没意识到她会很出彩?
耿军:我拍的时候快冻死了,我在里面不是也演了一个角色吗,最后倒地上了,我们拍的时候是3月,雪虽然很大,但是你一倒下,在那儿躺一会儿,身体的热量会把雪融化。之后,你的后背整个是一个硬板,一会儿化掉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化掉一会儿站起来,整个都透了。我在那儿演也没法看监视器,其他的演员在那儿看监视器的时候,他们会笑话,说我演得太烂了什么的。其实我自己拍的时候,真正感受就是天气的、物理的那些东西。
当下需要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审美
新京报:大家有时会过度解读你的作品,甚至与你本意完全相悖,看到这类评论时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耿军:其实别人对我的评论我不太看,有的时候,朋友看了转给我,我才能看到。电影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其实是一个自由的舆论场,你想说什么都可以,你理解、误解、费解都可以。所以在这个点儿上,它对于观众和作者是公平的。
新京报:但你是个作者性很强的导演,作者性意味着强输出,与之呼应的是准确地接受,任凭他人解读的话,这是不是有一点儿矛盾?
耿军:不太矛盾,一个人叫自言自语,被议论就证明它已经形成了那个讨论,证明这种内容输出已经完成了,这个东西都已经建立了,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就不用担心了,这关已经过了。
新京报:对创作者来说,某一瞬间与观众形成了同频,有了共鸣,应该是非常爽的一件事。
耿军:对,我在影院体会过。金马期间放《轻松+愉快》,演到教徒小二跟骗子相遇的时候,影院忽然特别喧哗,大家觉得,哇,太过瘾了。但我自己不知道会出现这个情况,我预料不到他们会喜欢这个情节。后来映后交流,我能体会到那种共鸣和他们的兴奋,都是我意料之外的东西。看到这些反应我的真实想法是,拍电影还能这么幸福?
新京报:你在《一席》演讲时说,最开始拍完《烧烤》,在电脑上看大家都觉得不行,根本没法看,你很失望。后来在大银幕上,有观众在场的状态下,大家感觉又不一样了,都觉得挺好。那你评判自己电影的标准是更倾向于观众反应,还是电影自身的质量?
耿军:其实我对于自己的作品可能没法特别理智,也没有办法特别客观地看待。生活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好电影看得太多了,所以在创作上自信也好,自我怀疑也好,这些都特别正常。但是我可能会自我怀疑多一些。
新京报:但你的风格一直非常确定。
耿军:我怀疑的不是风格,我的自我怀疑其实是在每一部创作的时候,那个探索的部分,我会想怎么才能让自己的创作在探索上再稍微有一点儿新的可能性。这件事上其实是我最兴奋的,虽然也会自我怀疑,但这是一个正常的创作心理,只是我的自我怀疑可能比外界看到的那种状态更严重一些。
新京报:无论文本创作,还是视听语言上的怀疑和探索,有没有想更融入大环境的原因?
耿军:不会有这个原因。它不会不融入,因为这个时代里同质的东西太多了,挺需要有个性的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审美出现。这一点我倒没有任何怀疑,我还挺自信的。我怀疑的其实是自我要求那部分,有点儿像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要求。你知道我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在创作的时候,接近于我对另外一个人的要求。
新京报:自我要求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一定会有变化,尤其电影是集体劳动,最终的作品往往是妥协的产物。
耿军:但电影也可以现场产生创造力,在现场,你跟摄影,跟演员都会有一些即兴的东西出现,这些东西是从剧本溢出来的,当你捕捉到它们,会是特别美好的时刻,我的作品,所有电影作品都会保留这些。
新京报:即兴部分在你作品中比重大吗?
耿军:不大,每次开拍之前,我其实对台词,对人物关系什么的都已经弄得很瓷实了。所以如果演员在拍摄的时候想要改里边的词其实很难的,能改吗?能改,但是很少的地方能改,大部分是改不了了,因为已经深思熟虑了。我说即兴的部分,不是剧本上的,是在现场拍摄时大家会碰撞出来一些东西。
那些不屑一顾的东西,才是我最在意的
新京报:在《锤子镰刀都休息》里,有一个情节是三个主人公分别受挫后回屋里坐着,气氛伤感,一人开口说我跟你俩说说我家里的事,另两个立刻表示不愿意听。当时觉得你挺狠的,拒绝温情,不美化生活。
耿军:我觉得这是我看待世界的一个基础,不美化也不丑化,这两个点放在一起是很难的,因为都是个人判断,那我就想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就是没有办法美化我熟知的一切。
新京报:在很多东北题材电影里,创作者都会有意无意地加入一点儿温暖的东西,稀释沉重,而你很明显地要把这些唾手可得的温情撕碎。
耿军:我觉得这个来自于我对自己的态度,我对自己不客气,我也没有办法同情自己,我觉得任何一个现实局面都源于互动和共谋。你说的这部分是我的自我认知,我会让这些溢出银幕,否则我会觉得拍得不够意思。我要把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在电影里面呈现出来,这个呈现是私人的。虽然我总说自己是感性支配创作,但电影成片终究都是有意为之,因为它不是一个单一镜头的监控,镜头组成电影后要把设计感抹平,才能让人物在里面活起来。展示他们的性格,他们的能力,他们的无能,他们的柔软,他们的虚伪,他们的狡诈和他们的温情,可尽管那样,他们也需要拥抱。
新京报:把抢劫当手艺的劫匪,抢劫未遂会感慨手艺生疏。这种荒诞的设计,似乎又藏了点儿柔软的东西。
耿军:有时我会想,我们生活那么不堪,但舞厅还开着;我们生活那么不堪,但是冬天喝完酒以后,会觉得地是软的。这时候抬头看看夜空,看看星星,心也会变得特别软。这些东西在生命里的每一刻,都会有层次感。所以那些浪漫的,那些优雅的,那些柔软的东西,也会出现。
新京报:但在关于东北题材的电影里,优雅和柔软并不多见。
耿军:我觉得眼光必须要跳开,否则就会陷在里边,电影不单单是一个地区性的或者一个区域性的表现,对我来说电影是人类的,我从来不觉得我的电影就是一个东北量贩作品。
新京报:你的电影有时会让我想到一本小说《罪行》,冷酷、戏谑,态度明确。
耿军:我看过那部小说,其实呈现这样的事,这样的态度,就是我创作的兴趣。我不愿意指着对方鼻子,指着对方脑袋,指着对方心脏的位置骂街,我不喜欢那样的方式,我喜欢绵柔一点儿。其实大家往往会特别在意那些内在的东西,而不是表象的东西。内在部分在写剧本的时候就已经成型了,但每一个阶段我都对这个时代有自己的看法,这些东西其实是我创作里边很重要的一部分,逃离不开。
新京报:在你早期作品《青年》中,你质疑爱情的代价,质疑兄弟义气到底是什么,在那之后,你的作品虽然看似变得温情,但本质上却更加冷酷,因为你对他们的悲惨都开始质疑。
耿军:对,因为其实到后来,我对世界的认知,打开得越来越大了,我想让作品更宽广一点儿。这种想法在每一个作品里能渗透多少,我自己没有一个理性的分析。但这些东西一定会以一种优雅的方式,或是以一种温柔的方式表达。
新京报:这些表达方式的外在更像不屑一顾。
耿军:其实我拍的所有不屑一顾都是我最在乎的东西,真的不屑一顾,我早就不干了。我觉得,只有当你对这帮人有特别浓重的情感时,才能拍出这种所谓的不屑一顾,是因为我在意才这样,我在意难道要我深情对它诗朗诵吗?不是,我用我另外的方式在意它。(创作)根源上那个东西是特别模糊的,但我那个根源,自己非常清晰。
东北青年作家崛起,是这个时代的荣幸
新京报:你的电影作品中的人物都很江湖,但他们又从来不与权力相关,就是人的关系,人性的互相钳制。
耿军:对,一个厂区会有一个江湖,一个社区会有一个江湖,一个煤矿会有一个江湖,可能邻居之间都有一个江湖,所以那个东西其实是民间的道德行为约束的一个东西,离我们生活非常近,看你怎么去表现。单田芳评书里会经常说这句话,叫“钱压奴婢手,艺压当行人”,你是有钱人,给你服务的就是你雇佣的人,那是雇佣关系。在一个行业里你做得好,很多人会收敛起平常的嘴脸,把最殷勤的部分露出来,因此江湖有特别不堪的,也有特别可爱的那一部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是最基本的伎俩,所有这些综合起来才立体。我的江湖不借鉴任何东西和类型,江湖就是我对世界的看法。
新京报:你怎么看之前一些东北题材的电影?
耿军:我觉得像张猛、王兵他们的作品都对当时的时代有特别好的描述,我特别喜欢那些东西,那是描述东北非常重要的作品。还有许鞍华和陈果,其实他们的作品更善于捕捉,是对人和在那个环境里的挣扎和不堪、彼此依赖非常扎实的捕捉,外来视角往往更加精准,这两部作品都是被导演的能力和热情点燃的。我疫情期间重看了一遍《榴莲飘飘》,还是特别喜欢。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导演是在利用东北,但那些东西终究会被淘汰和淹没。
新京报:这几年媒体无数次提到东北作家崛起。像班宇、双雪涛、郑执,还有同为沈阳人的作家苏方,他们的年龄与成长背景都有些相似,作品又完全不同,很想知道你怎么看待东北文学以及文艺复兴这些概念。
耿军:我觉得2000年前后,也有好多东北作家,刁斗、洪峰,包括后来给姜文写剧本的述平,还有全勇先。再之前有马原、皮皮、迟子建等,这些作家其实一直在持续创作。这几年新出来的这几位东北作者,是一个延续。我觉得当纸媒、纸制品、图书到了现在这个特别艰难的时候,有这几个人出现,能让好多人重新买书看,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用现象可能不太准确,我觉得这事本身就特好。我跟他们面对面聊天的时候也丝毫不掩饰我是他们的书迷,虽然他们算同龄人,也是老乡,但每个人的角度和风格都不一样,又都足够好。我觉得他们能出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荣幸。
新京报:你目前所有电影都是自己编剧,为什么没有想过改编小说?
耿军:我后面的电影是改编作家刁斗的小说,但剧本还是我自己写,我一直挺谨慎地看待改编这件事。因为我有点儿怕辜负了人家那么好的小说。我自己写,辜负我自己没有任何歉意,我对小说、诗歌都有一些敬畏之心。
听到“鹤岗宇宙”这个描述,挺高兴
新京报:现在年轻人喜欢讨论去鹤岗买房,当个小镇青年,其实你的电影最开始就是拍的小镇青年,这些曾经的小镇青年也一直陪伴你到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可以说你的电影是对小镇青年的长期记录?
耿军:这次《东北虎》对我最特别的在哪儿呢,我把《散装日记》《烧烤》《青年》《轻松+愉快》的所有演员都集结到了电影里,是我自己这十多年用过的重要演员集体亮相的一部电影。这被观众延伸出了一个词“鹤岗宇宙”。虽然其他的导演或小说作者通过作品呈现了一个什么区域性的什么宇宙,但我自己没想过这事,他们给我这个描述我挺高兴。
新京报:也是因为你在电影中构建了一个很坚固的家乡体系。
耿军:是,我对家乡和对跟我一起成长起来的演员,是互相依赖的状态。我觉得电影是脸的艺术,一个单独的人,他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拍他,到现在四十多岁我还在拍他,我觉得这种持续地关注、持续地呈现是非常有趣的,他们的容貌在随着时间变化,但又是他同一个人。你看《青年》的时候,刚哥、勇哥、袁利国,他们是什么样的。看到《轻松+愉快》和《东北虎》的时候,他们又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我在意的,也是我审美上的一个东西吧,我经常会说,一个演员好看,那是一个消费层面的东西,但我会说我的演员漂亮,那是审美层面的,因为他们在银幕上出现的时候真的很有魅力。这是来自于面孔跟岁月综合形成的魅力。
新京报:你电影里的这些主要演员也是你生活中的伙伴,即使他们都是非职业演员,你也说过无条件信任他们,是因为有共同的生活背景,所以他们更容易理解你想表达的东西吗?
耿军:不,我从来没有求过理解,我自己都不理解我自己。人跟人之间能要求理解这件事是很变态的,当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说理解你,这是一个要挟,接近于情感绑架。
新京报:他们也不需要理解你的作品?
耿军:他们可能也不太重视作品,作品对他们来说不重要,他们会直接表扬说,老耿这把整得挺好,我也会客气地接一句说我也觉得弄得还行,仅此而已。大家会聊作品内部的什么吗?会聊,勇哥演得不错,也只是这样非常简单的交流。身边眼前都是熟悉的人,你说演得好跟谁对比?没有对比,这种夸赞是出于友情的。
新京报:但创作者一定都有创作的虚荣,很难有人避免。
耿军:都会有。我知道自己的虚荣在哪儿,就像你跟我聊到“有几场戏,很长时间都能记得住”,我的虚荣心就会起来,我说这哥们儿对这个感兴趣,但是那个确实挺精彩的,这种东西特别自然。但每天所有的热闹散去,马上要躺下来睡觉的时候会在脑子里过一下,一切只是挺有意思而已。
新京报:这种自省是你个人的要求,还是团队都如此?
耿军:演员可能在一个中间点上。很难拿捏这个点,如果不自知,他们在演技上不可能进步这么快,其实不自知也没事,人的内心形态没有太大变化就可以。比如说我们去了电影节,之后其实有一些人会比较膨胀,我就特别自然,我说“我膨胀一周或者最多两周”。完了刚哥说,“哥,我得膨胀一个月”。我说,“那你就按照一个月膨胀”。
电影是“巫术”,我在创作上从没顺过
新京报:你的电影经常得到评论和奖项的肯定,但你的名字对大部分观众来说却很陌生,你的导演之路似乎比同时期导演要曲折一些。
耿军:每个人的创作都没有那么容易。我比别人更不容易吗?也没有。就比如跟我创作时间差不多长,作品跟我都是同步成长的导演,他们稍微早一点儿拍了所谓的市场作品,我觉得这是人家的选择之路,特别自然,只要他们创作还能保持一个挺好的状态,我就觉得挺好。
新京报:《东北虎》在2012年就写了初稿,但受限于条件没有机会拍摄,面对这些也一直坦然?
耿军:我2012年虽然写了初稿,但那个东西有多成熟吗?没有多成熟。我找不到钱那就意味着片子现状不太理想,或者是我个人的数据不太够。凭什么你想找着钱就能找着钱,凭什么你想拍就能拍,电影院又不是你们家开的。这个东西我拎得特别清楚,我觉得持续拍是最重要的,我不是那种消耗在一个项目上的人。
新京报:你前期后期作品风格转变很大,对你个人来说,哪个阶段更顺一点儿?
耿军:其实对我来说,这些年最长的拍摄两个月也就完了,片场我又不陌生,早些年做副导演,后来自己也拍了几个,技术层面没有多难。我以前经常十来个人拍,《烧烤》的时候只有五六个人,《东北虎》现在一百多人拍。没有哪个电影是特别容易拍下来的,也没有哪个电影觉得会顺,我创作上没有顺过。
新京报:当不顺的时候,你对电影和自己能力的看法有没有产生过变化?
耿军:我一直觉得电影是巫术,不太能用现实生活考量。你想想它能调动人的情绪,调动人的情感,能在屋子黑了后,在大银幕呈现另一个世界,对我来说它是巫术。
新京报:《东北虎》算是你第一部真正意义上有女主角的电影吗?
耿军:我之前的作品里,确实女性角色不多,因为我对女性没有那么了解,在我身边,哥们儿这个群体占用的时间更多,所以在作品里就比较少呈现女性。《东北虎》这次确实是女性角色戏份最多的。我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她们有了一些了解。当我了解一些后,我才会平衡这个故事。因为女性在现在这个社会体系里,承载着一半甚至一大半,所以虽然说现在是男权社会,但我觉得它是母系社会。
新京报资深记者 汤博

标签:

 酒业新闻
酒业新闻 茶业新闻
茶业新闻 食品新闻
食品新闻 酒知识
酒知识 茶知识
茶知识 行业展会
行业展会 茶道文化
茶道文化 茶艺
茶艺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