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帮女人的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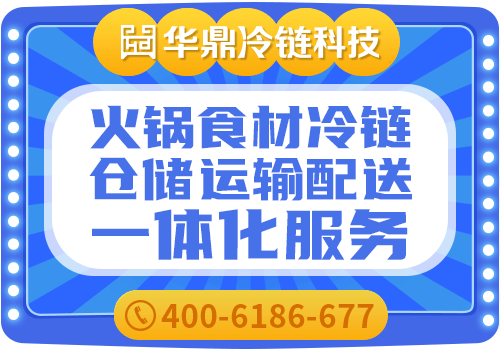
许多年以后,当我重数年轻时等待打下的草结时,我会想起那个大风沙的下午,我送阿错出行时的情景。
那天皇历上写着:无风。大吉。益出嫁,远行。
无风的日子起了大风,不过父亲说,那风是顺风,易行。
阿错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那是一个连父亲都没有去过的地方。听说,那里的人跟我们这里长得都不一样。
阿错走的前一夜,我一直在磨刀。刀是父亲的。20年前,父亲也是一个马夫,他用一把短刀割断了一土匪的喉咙,然后从他手中带回来了这把长刀。父亲说,这是一把纯钢打造的刀,在我们这个地方根本买不到。连见到的机会都不多,他带着这象征着胜利与荣誉的刀又过15年,直到母亲下葬的那天才解下。
再后来,他在我16生日的时候送给我。当时我不明白,我是一个女孩子,也要用刀吗?直到阿错出现。
在我母亲的叙述里,当年父亲的那一仗,打得天地失色,日月无光。父亲一行只有10个人,而来打劫的土匪却有30多个。马锅头见形势不对,迅速上了最快的马,独自跑了。剩下的九人被土匪们包围了起来。有人已经跪下去投降,有人交出了刀,还没有正式开战,马帮们就输了一半。
但是,父亲没有退缩,他一出刀就砍到了两个人。受到鼓舞的其他马帮也振作起来,投入到战斗中。父亲砍到第6个人的时候,满身都是鲜血。
母亲说,当时父亲才像个没有天性的土匪,他完全红了眼。他的疯狂同样吓跑了胆小的土匪,也鼓励了其他战士。父亲一共杀了16个土匪,为此,他也付出了左手被砍的代价。
清理尸体时,父亲在林子里发现母亲,她被布捂住了嘴,绑在一棵树上。土匪头子想把她抢回去做小老婆。而她的家人,已在土匪刀下饮恨而终。父亲带走了土匪头子的刀和本应该属于他的女人,继续上路了。
再后来,父亲作为一个传奇,开始在那线路上延伸着。一些遇到土匪的马帮,只要抱出父亲的名号,他们便知趣退走。一个参与当年马帮战斗的叔叔告诉我,在父亲建议下,他们当时不仅葬了自己的兄弟,还葬了土匪,即使是土匪身上的财物,他们也尽数下葬。
这是一个连土匪都感动的故事。
父亲娶了母亲后,给她开了一个茶铺。关于父亲和马帮的故事,我就是在茶铺上听到的。母亲说,马蹄声是世间最美妙的音乐,当时,我听不出。我只知道,马一过,尘土飞扬,许多人都要换水。
直到我等待阿错的日子,我才明白母亲这话的深意。
五里之外,只要有马蹄声传到,我就准备好茶杯。每听到一次,我就打一个结。我希望,有一天,用这些打结的草编织一个花环,带到他的胸前。
5个、10个、15个……
有一年春天,又一队马帮过去后,我来到了山上。漫山遍野都是红红的杜鹃花,红得如同血色,如同胭脂,如同一个女子兴奋时泛起红晕,一波波地延伸着。在人迹稀少的茶马古道上,突然惊艳,大喊,然后闭上嘴巴。
太有期望的一切,都是瞬间便消失的。如同那杜鹃,如同刚刚过去的马帮,转过身去的时候,他们都不在原来的地方了。
那一天我大哭了一场,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床上。父亲说,我沉睡了一天。
第二天,父亲也上路了。他许诺于我,会把阿错带回来。
于是,我的手上又多了一根草绳。
皇历又翻了一页,新的页面上写着:小雪。凶。不易喜庆。
父亲的棺木是四个人抬进来的,他们说发现父亲的时候他已经僵硬,面目全非,若不是他那独特的断手,我就永远都见不到他了。
父亲的死是意外的,他们说他的身上并没有伤,没有打斗的痕迹。他们也设想,父亲可能是走着走着就倒在路上,再也没有爬起来过。父亲死在了自己走过无数次的路上,是他们安慰我的理由。
那天是茶铺惟一没有生意的时候,大家都带来自己的酒。我也喝了许多,有人告诉我,我流的泪比我喝的酒多。
父亲留下的文字,上面有阿错的消息。那只马帮穿过越南后,就没有消息。
剩下的除了等待,还是等待。
再后来,又有人捎来消息,他看到与阿错一起出行的一个人。
我打的结已经够编织10多个花环了,我已经很熟练地编织像花一样的结。
我把以前编织得不好的结重新编织了一道,我知道,每一个结有几根草。
杜鹃花又开了,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些经常来茶铺里玩耍的孩子,我已经好多年不上山,才发现,这里也热闹了许多。周遍的人越来越多,来这里开铺子的人也多了起来,但开茶铺的却只有我一个。
我要等的那个人终于来了。
他带来了一把刀,我年轻时候无数次观摩和磨的刀。它还是那么锋利,泛着青光,岁月在它那里,没有痕迹。我轻轻往手上一划,它才显得和蔼可亲起来,那么近,那么温暖。
那个人说,他们遇到了火枪手。刀失去的威力,无论是什么刀,无论它以前有着怎样的辉煌和光芒,都不及火枪那瞬间灿烂。
那个人说,他得以幸免的原因是,他是土匪的后代,那刀是他父亲的,而不是我父亲的。甚至,他在一段时间觉得,我父亲才是强盗。
那个人说,后来他才知道,我在等着带刀的人。
可是,一切都不重要了,刚性的刀我已经陌生了。现在我熟悉的,只是柔软的草绳。那草,维系着太多的东西。
我把我多年来打的结做了一个大大的花圈,把整个茶铺包围起来。它们,本应该是做花环的。

标签:
上一篇:茶字流变
下一篇:返回列表

 酒业新闻
酒业新闻 茶业新闻
茶业新闻 食品新闻
食品新闻 酒知识
酒知识 茶知识
茶知识 行业展会
行业展会 茶道文化
茶道文化 茶艺
茶艺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